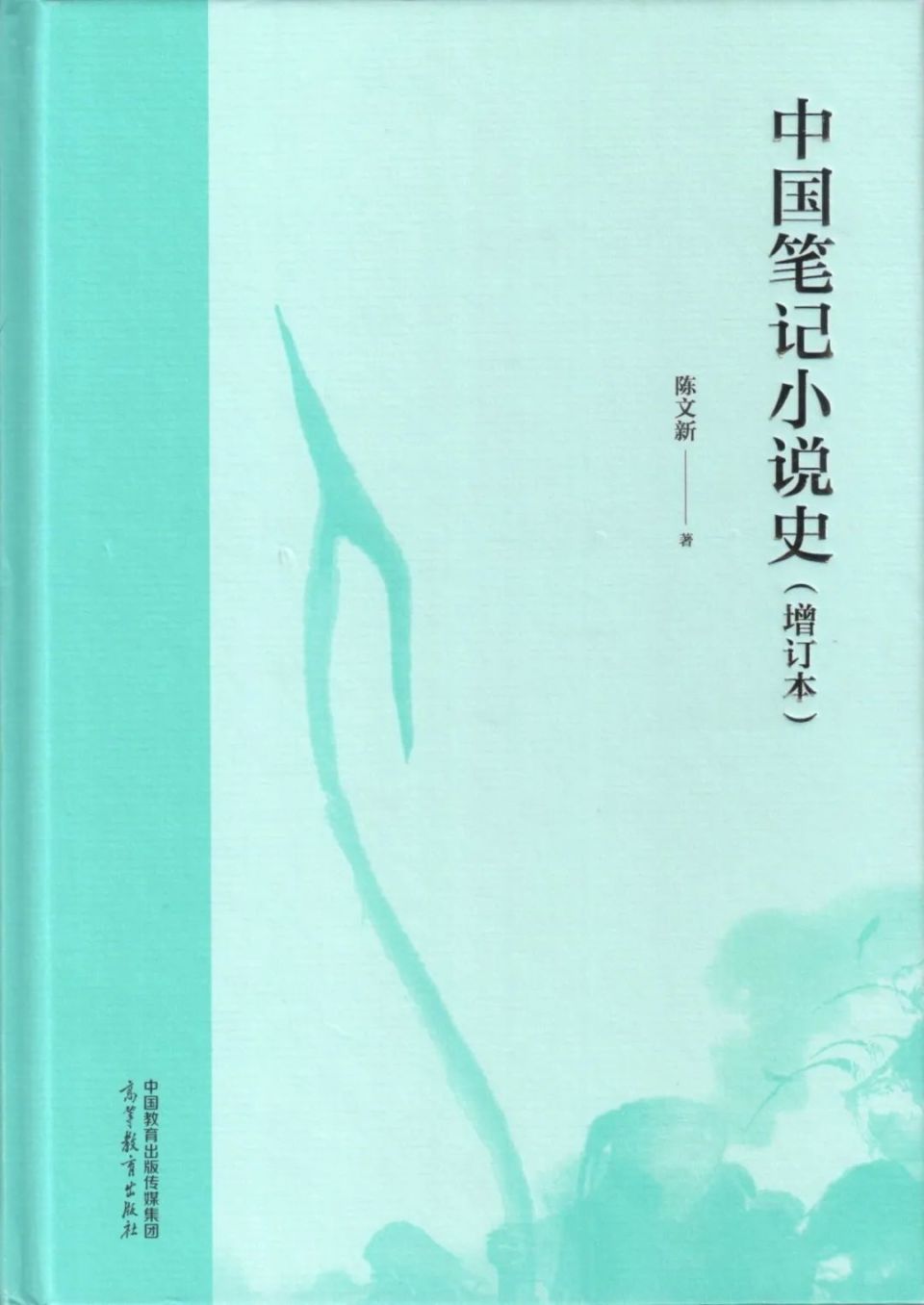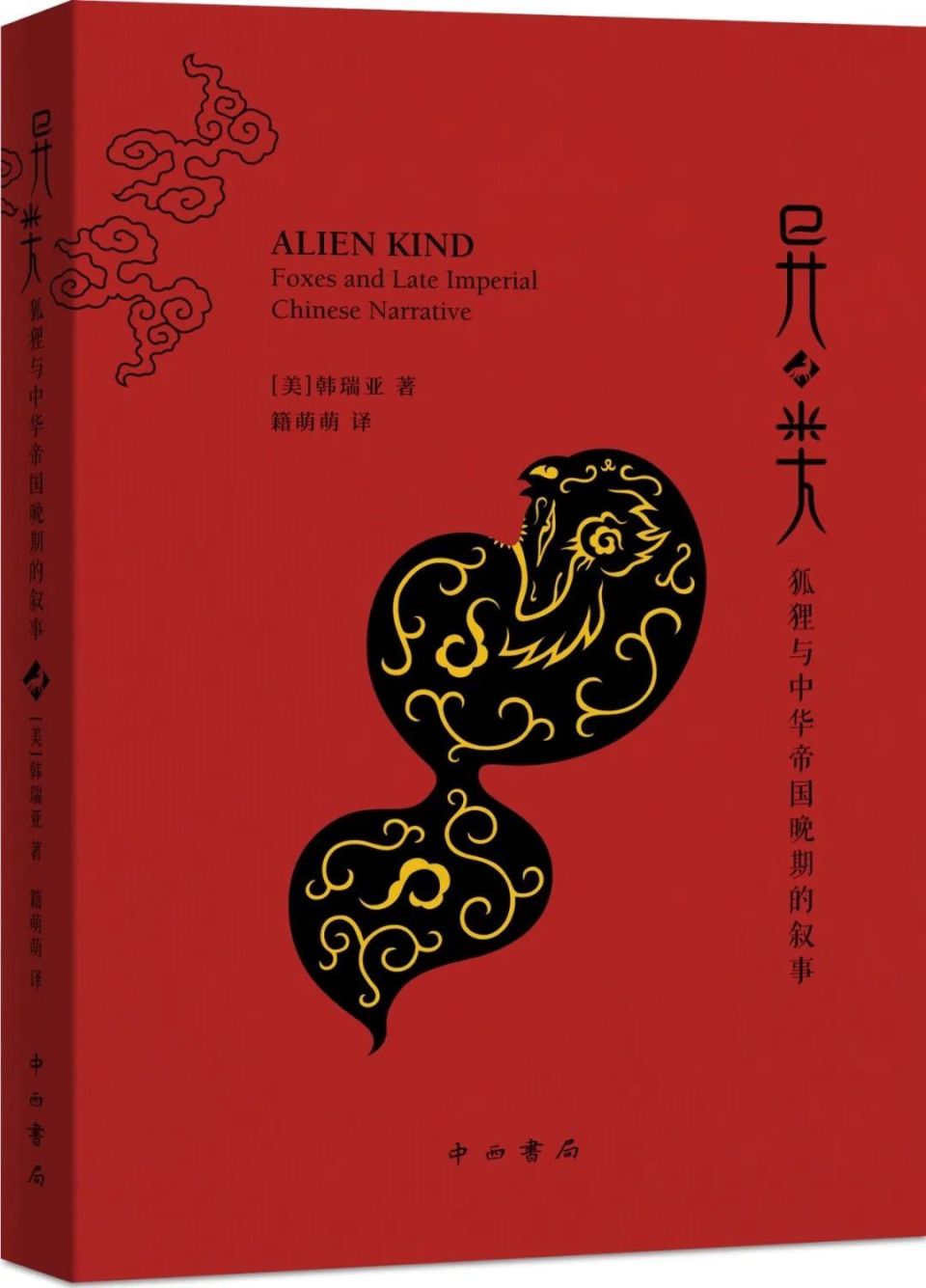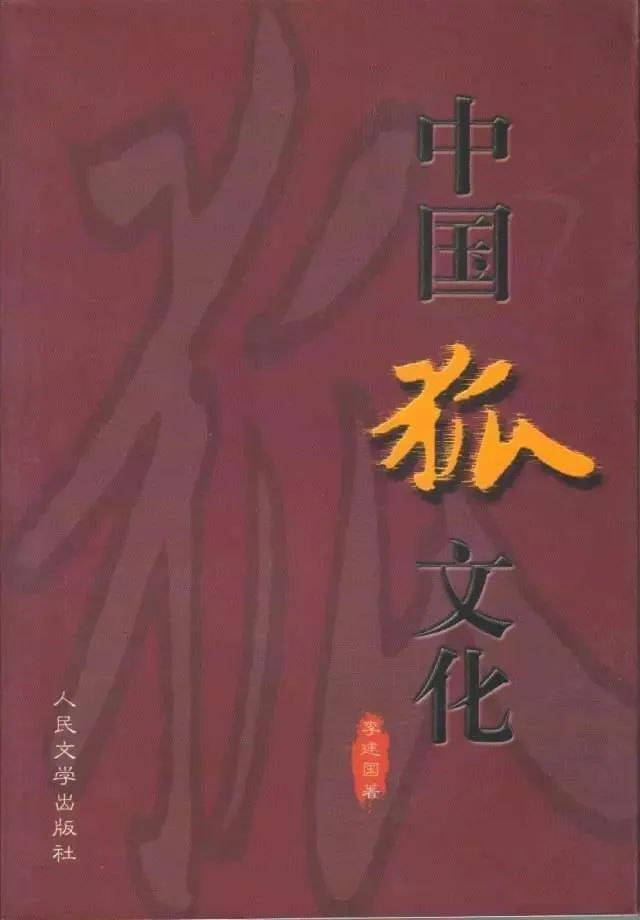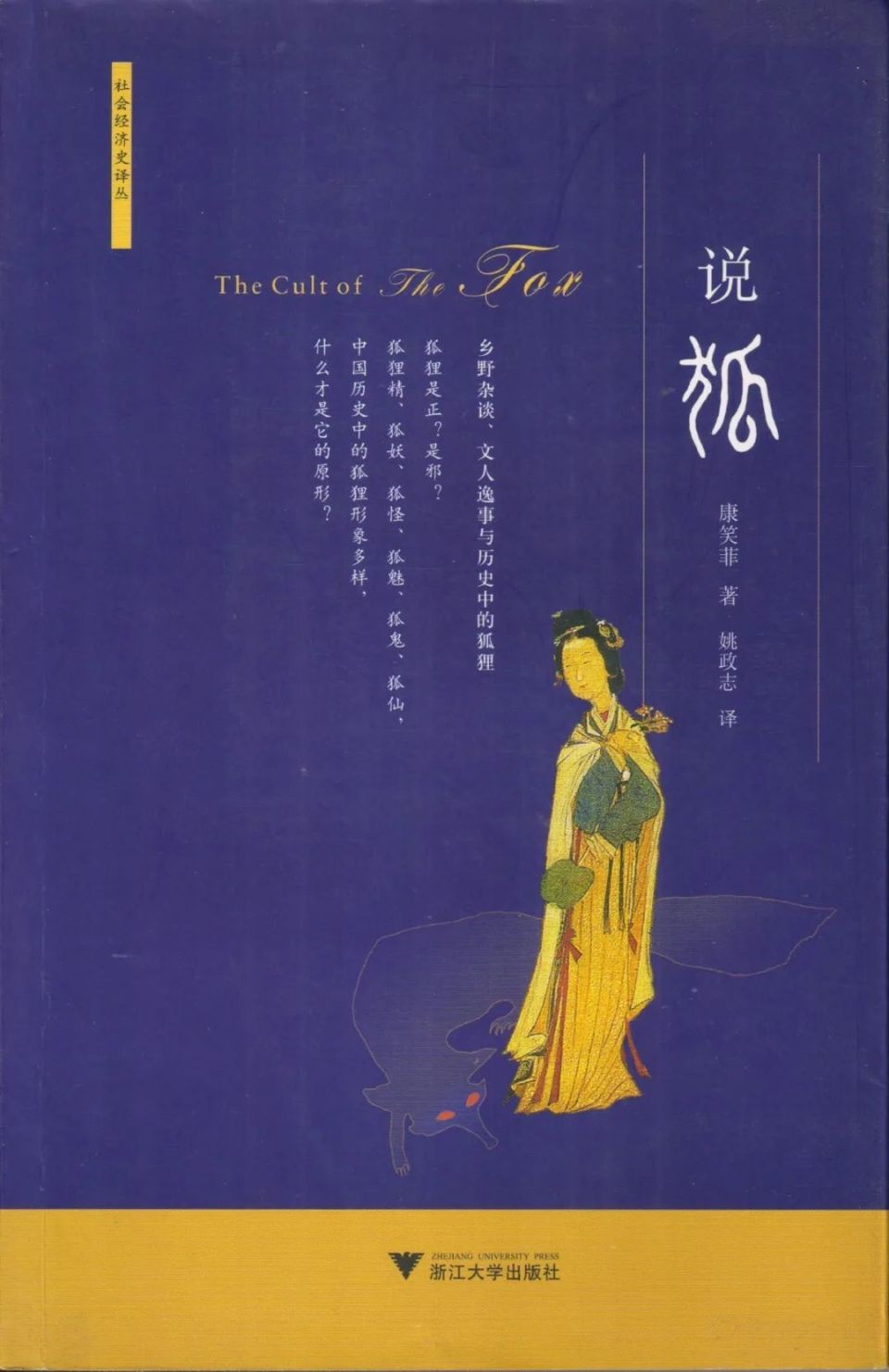明清时代,狐幻化为美女与人恋爱的故事,比比皆是,尤以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为多。纪昀反仿这一类故事,写丽女假托为狐,很能见出他的幽默与智慧。
比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三的一则:
游士某,在广陵纳一妾,颇娴文墨。意甚相得,时于闺中唱和。
一日,夜饮归,僮婢已睡,室内暗无灯火。入视阒然,惟案上一札曰:“妾本狐女,僻处山林。以夙负应偿,从君半载。今业缘已尽,不敢淹留。本拟暂住待君,以展永别之意,恐两相凄恋,弥难为怀。是以茹痛竟行,不敢再面。临风回首,百结柔肠。或以此一念,三生石上,再种后缘,亦未可知耳。诸惟自爱,勿以一女子之故,至损清神。则妾虽去而心稍慰矣。”
某得书悲感,以示朋旧,咸相慨叹。以典籍尝有此事,弗致疑也。后月余,妾与所欢北上,舟行被盗,鸣官待捕;稽留淮上者数月,其事乃露。
盖其母重鬻于人,伪以狐女自脱也。周书昌曰:“是真狐女,何伪之云?吾恐志异诸书所载,始遇仙姬,久而舍去者,其中或不无此类也乎!”
这一则包含了三个层面。
一、丽女假托为狐,以成其奸谋,故事寓有讽世之意。
二、周书昌据此推论,断言“志异诸书所载,始遇仙姬,久而舍去者”,其中可能就有这种情形,这是对人、狐恋爱故事的颇为高明的解构。
三、“狐化为美女”,这是一个已经老化的故事套路,经过人们的反复使用,已不能引起读者的新鲜感。
但老化的套路也可被赋予新意。有人曾经举过一个例子,“遍体鳞伤”译成英语的时候(be covered with bruises like the scales of a fish“身上伤痕遍布有如鱼鳞”),便重新以其鲜明的具象的悲掺令人震惊。
与这种从新的角度来调整语言结构的技巧相似,纪昀反用“狐化为人”的构思,变为“人托为狐”,经过他的“陌生化”处理,读者又被带回到了新鲜的感觉中。单凭这一点,纪昀就足以赢得喝彩。
就讽世而言,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二的一则足够辛辣:
京师一宅近空圃,圃故多狐。有丽妇夜逾短垣,与邻家少年狎。惧事泄,初诡托姓名。欢昵渐洽,度不相弃,乃自冒为圃中狐女。少年悦其色,亦不疑拒。久之,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:“我居圃中久,小儿女戏抛砖石,惊动邻里,或有之,实无冶荡蛊惑事。汝奈何污我?”事乃泄。
故事确凿无疑地寓有“人不如狐”之旨,如纪昀篇末所说:“人善媚者比之狐,此狐乃贞于人。”
比狐更为冶荡,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。
【相关阅读】
本文摘自陈文新《中国笔记小说史》增订本第十一章,经作者授权刊发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